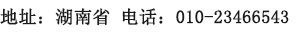史说渔港历史
沈家门渔港与海上丝绸之路
沈家门渔港,是我国古代对外开放港口明州港(宁波),通往高丽、日本必经航道,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早在唐代中期就已形成。唐显庆四年(),日本2艘遣唐使船,途遇风暴,其中一艘来到了须岸山(朱家尖)。唐咸通四年()日本高僧慧锷从五台山请得观音菩萨归国,从明州出发,先到沈家门,再至于梅岑山(普陀山),遇风暴,舟触礁后,只好留观音像于山上,渐形成观音道场。
《图经》一书记载了当时从明州到高丽的航道。明州三江口桃花渡或定海(今镇海)招宝山出发,过大浃门,过虎头山,到沈家门,再至普陀山,过海驴礁,到蓬莱山(今岱山),入白水洋、黄水洋、黑水洋,过白衣岛、苦苫苫、唐人岛、分水岭,入高丽礼成江,由陆路进入王城。
“对开两门,四山环拥”的沈家门,既是海内外船舶的天然良港,也是航海者祭祀岳渎之神的地方。元丰三年(),阁门通事王舜封,应高丽国王王徽所邀,出使高丽为王徽治病回国,途经沈家门外的莲花洋,遇到巨大海龟顶拱船只,王舜封立即遥望普陀山观音菩萨,进行礼拜,礼毕海龟才消失。为此,徽宗奉诏改赐“不肯去观音院”为“宝陀观音寺”。
明景泰四年(),日本遣明使允澎,率使船9艘,停泊于莲花洋,由沈家门地方派出百艘彩船,环绕使船列队欢迎,并赠送酒、淡水、食粮等物,进入沈家门港后,又有官员乘画舫50艘,吹角打鼓迎接,然后由巡检司官员作向导,进入宁波港。归国时,又有数百艘战船,数万海军士兵护送到沈家门,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。千年以来,沈家门港内曾经百舸争流,贡艘浮云,热闹非凡。
沈家门渔港开发史
明代时的沈家门港,只有今天的小西湖和新街周围的两个海湾,渔民基本上集中在泗湾、教场,依山湾、凿井而聚。从现存的龙眼井潭、陈家湾井潭、戚家湾井潭、缪家塘方井潭、泗湾双眼井潭等五口古井的分布上,就能看出“茅屋村村绕白沙”的原始民居格局。而在宫下一带,存在一个沈家门渡,舵岙、南岙、大蒲湾、小蒲湾等地的居民,都是通过此渡口与外面交往的。清康熙四十八年后,此渡口才向南移,成为后来的“大道头”。
明洪武十九年(),由于倭寇侵扰,清顺治三年(),由于明朝遗臣在此抗清复清活动,明清政府两度实行海禁,“午前徙者为民,午后徙者为军”,查村搜岙,见人就赶,将居民尽迁内地,仅少数逃入深山者留了下来。沈家门二度成为荒无人烟之地,印证了沈家门“成名早,开发晚“的老话头。
清康熙二十二年(),台湾平定,次年朝廷颁布“展海令”,展复舟山,召民开垦,自此沈家门居民纷纷返回重建家园,同时带动了镇海、奉化、宁波、温州、台州等沿海各地人民迁入。从此,沈家门居民凭借独特的天然优势,操舟弄桨,撒网捕鱼,辛勤劳动,唱响了一部沈家门渔港的开发史。
清康熙四十八年(),舟山迎来了一位名垂青史的知县缪燧,他发银先后修筑了东横塘、西横塘、荷叶湾塘、墩头塘等海堤,岸线相连、挡潮水与塘外,泊渔舟于岸前,平地面积大幅度扩展,基本形成了今日沈家门港区格局,为随后百年沈家门渔港的拓展和繁华创造了基本条件。
沈家门渔港正式形成
至同治年间(-),沈家门渔港开始真正形成,渔业兴旺、商贾衍生,集市渐兴,水产品、农副产品多在街头设摊交易,并于光绪年间始称为镇。光绪九年()编修的《定海厅志》载:“沈家门镇每岁春季渔船停泊之所”,港内停有福建、勤县、定海等地的渔船近艘,人口达余。
清光绪三十三年()编写的《定海乡土教科书》中称沈家门:“市肆骈列,逼临港口,最便运输。交冬令,闽舟之捕带鱼者,栖泊与此。海物错杂,贩客麇至,更为繁盛。港至南以户家屿(鲁家峙),为寄碇胜地。”这时的东横塘、西横塘即现今的东大街、西大街,为海岸最前沿,为渔港最繁华的地方,堪称清代的一条沿港马路。民国初海涂又涨,渔港外延,慢慢贯通东边的茶叶湾和西边的墩头外塘,形成了更长的岸线。
至民国13年(),已是“冬季值渔汛,帆樯如林,街衢廛舍,鳞次栉比”。民国25年(),已有鱼行栈多家,从业人员多人,上海《申报》载“浙省定海渔业,冠于全国,而沈家门地方,尤为渔民荟萃之区,每届冬汛,有大对船一千二百余对,放洋采捕”。
新中国成立后,沈家门渔港达到了历史最高峰,与挪威卑尔根港、秘鲁卡亚俄港并称世界三大渔港。国家先后多次拨款,拆除沿港低矮民房建筑,拓宽沿港路面,顺直岸线,直达半升洞,并筑石砌砖护壁,疏通港道,整修码头百余座,形成了当今的滨港大道。每当渔汛旺发时,渔港内停泊着近万艘渔船,流动人口达10万以上。华东六省一市都在渔港设置了“渔业指挥部”。
文:石村
图:石一村平姜艳
天气预报
欢迎